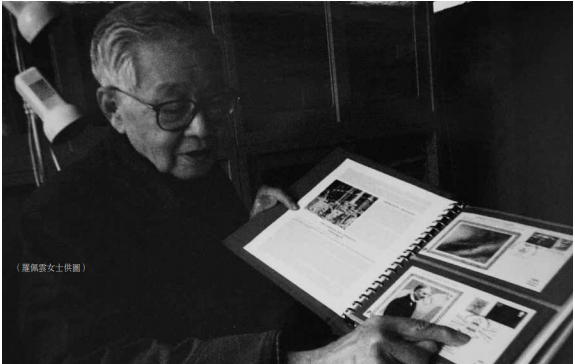主欄目:《香港文學》2018年7月號總第403期
子欄目:悼念華語文壇泰斗劉以鬯先生特輯
作者名:蔡益懷
劉以鬯先生在我眼中是一個孤獨的文學漫遊者,因「與眾不同」而煢煢孑立。
當然,我也知道他是香港文學的一個代表性作家,在當代文壇享有盛譽,倘以「文學先鋒」、「文壇教父」來形容大概也不為過。
我這樣說不是胡亂送高帽,而是基於個人的閱讀和認知。從1948年由上海南來香港,劉以鬯先生一直從事報刊文學編輯和創作,是香港文學的重要參與者,其作品如《酒徒》、《對倒》、《打錯了》等,已成為香港文學的經典之作;而同時他又是香港現代文學的重要推手和見證人,許多重要作品都經由他的手刊發,如也斯的《剪紙》、西西的《我城》,都是發表在他主持的《快報》副刊。縱使在2000年離開《香港文學》,告別編輯生涯,他在文學界仍發揮着相當大的影響力,引領了一代又一代文學人,為業界所推崇。
從文學史的定位來說,劉以鬯先生之於香港文學的一大貢献,是不餘遺力地推動嚴肅文學,尤其是現代主義文學的發展。這對於一個身處於商業文化夾縫中的文化人來說,殊不容易。在一個被金錢所支配的社會,文化人首先面對的是生存的困境,沒有任何做浪漫化的文學夢的空間,也容不得任性。正如他自己在《酒徒》中所言︰「這是一個苦悶的時代,每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都會產生窒息的感覺。」而就是在這樣的現實狀況下,他仍沒有放棄自己的文學夢,而以「適者生存」的法則,用兩隻手寫作,一隻手寫「娛樂他人」的東西,一隻手則寫「娛樂自己」的文字。
在「娛樂自己」的創作中,劉以鬯走的是一條先鋒的道路,作了大量的現代主義小說實驗,成為香港文學的一個異數。他的現代文學意識,在《酒徒》中已有明確的宣示︰「現實主義應該死去了,現代小說家必須探求人類的內在真實」;「探求內在真實不僅也是『寫實』的,而且是真正的『寫實』」,「必須放棄表面的描摹,進而作內心的探險」;「文學是一種創造,企圖在傳統中追求古老的藝術形式與理想,無論怎樣熱情,也不會獲致顯著的成就。現實主義早已落伍,甚至福樓拜也說過這樣的話――我們手邊有複音的合奏,豐富的調色板,各種各樣的媒介……但是我們缺乏的是︰﹙一﹚內在的原則;﹙二﹚事物的靈魂;﹙三﹚情節的思想」。可見,他不甘於走傳統寫實主義的老路,而是追求「與眾不同」的新路,如《天堂與地獄》、《對倒》、《打錯了》等,在敍述手法上都是出新之作。他自己常說︰「新的小說不一定好,但是好的小說一定會有新的意味在裡面,那不會是舊的東西,因為舊的東西只是在一直重複,這不會是好的小說」。
劉以鬯創作於1950年的〈天堂與地獄〉,以一隻蒼蠅的視角觀察世象,並以極富寓言色彩的筆調表達出作者對齷齪現實的諷刺。蒼蠅生活在一個可謂地獄的「齷齪而又腥臭的世界裡」,「這個世界,實在一無可取之處,不但覓食不易,而且隨時有被『人』擊斃的可能。」牠「怨透了」「這樣的日子簡直不是蒼蠅過的」世界。這個地獄般的世界其實隱喻的就是戰後的香港現實。對於一隻蒼蠅來說,有冷氣的咖啡館就是天堂,但是在這個「男『人』們個個西裝筆挺、女『人』們個個打扮得像花蝴蝶」的「天堂」中,蒼蠅看到的卻是一場「你騙我,我騙你」的鬧劇,所以,就連「我」這隻蒼蠅都「覺得這『天堂』裡的『人』,外表乾淨,心裡比垃圾還齷齪」,「這個『天堂』,齷齪得連蒼蠅都不願意多留一刻!」可見這個人間的「天堂」比蒼蠅的地獄都不如,這對於香港的社會現實無疑是一個絕妙的反諷。在這篇小說中,人都是加引號的人,又無疑是對人的本質的一種質疑和反詰。這篇小說篇幅雖短,卻透射出一個嚴肅而重大的主題──對天堂與地獄的反思,事實上這「天堂」與「地獄」也成了我們考察香港主題的一個關鍵詞。我想,這也就是劉以鬯這篇小說所蘊含的超時代意義之所在。另外,這篇小說的敘事視角也是值得一提的,「我」這種敘事視角原本是一種頗受限制的視角,然而,在這篇小說中,作者透過蒼蠅這個「我」去觀察、偷窺,卻擴大了這種敘述視角的表達範圍,蒼蠅可以飛到婦人頭髮上的絲絨花上偷聽,如此近距離的觀察,原本是無所不知的上帝視角才做得到的,由此可見作者的匠心獨運。
再如創作於1983年的極短篇小說〈打錯了〉,採用了反覆敍述的手法。故事中的人物陳熙從美國留學歸來,一直沒有找到工作,這天接到女友的電話,趕赴「利舞台」看電影,一出門就遇到車禍。但故事並沒有完,作者重新敍述了一次故事,這次,陳熙在出門前接到一個電話,耽擱了時間。結果這個「打錯了」的電話救了他一命,他避過了車禍意外,而且目睹兩個人橫死街頭。這個作品讓我想到德國電影《疾走羅拉》﹙1998﹚,都是以反覆敍述的手法,表現人的命運。這兩個作品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劉以鬯的小說比電影早了十幾年,可見劉氏的創作形式一直走得很前。
劉以鬯的實驗小說是香港現代主義文學的一大收穫,而《酒徒》正是香港文學現代轉型的標誌性作品。要準確理解劉以鬯的文學成就,及其創作的文學史意義,需要將他的創作放在整個文學語境中來考察。
從香港文學的發展脈絡來看,現代主義文學在香港的興起,絕不是一個異數,而是香港文學發展進程中的一個必然階段,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發展進程中的一個必然結果。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工商業逐漸發達,隨着社會環境的急劇變化,社會分工的日益深化,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不斷加深,個人主義漸成風氣;另外,從意識形態來說,這也是一個不同文化交融、碰撞的時期,中國傳統文化和民族主義的思想儘管仍大行其道,傳統的倫理觀和價值觀也還佔居主導地位,但隨着教育的普及,英語成為新興的語言,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日漸西化,崇洋風盛,西方的電影、音樂、時裝等流行文化深受歡迎,西方思潮如存在主義、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等席捲文壇,如此等等的社會文化現象,反映在創作上便形成了一股表現自我、崇尚個人體驗,表現孤獨,揭示內心矛盾的文學風氣。
由於工商業的蓬勃發展,市民生活水準的不斷提升,社會生活形態和個人的精神狀態也相應發生變化,這個城市「開始麻痺」、「生活中契約越來越多」,人們變得缺乏安全感,內心變得無所依歸,簡而言之,「人性改變了」。作家們敏感地感受到這種變化,開始以一種內省的方式表現人的內心掙扎、自我分裂,以及尋找身份,尋找出路的生命歷程。作家們不再滿足於以傳統的藝術形式「反映」現實與人生,紛紛作出新的實驗,嘗試新的表現手法,並產生了大批形式標新立異的作品,其中,劉以鬯的《酒徒》由於成功創造了一個人格分裂、精神沉淪的都市漫遊者形象──酒徒,而成為這個時期最有代表性的佳作。而崑南的《地的門》則通過青年葉文海所受的社會桎梏和束縛,反映了年輕一代沒有出路的苦悶,這個形象且成了港式「憤怒一代」的影子。這兩部小說在表現港人的生存狀態上都展示出了新的審美原則,揭示出這個都市新的時代病,流露新的都會意識。這個時期劉以鬯、崑南等人的現代主義的實驗性創作,無疑為香港小說帶來了新的氣象。如果說五十年代的寫實小說更多的是,以照相式的方式見證歷史、記錄歷史、審視社會歷史問題的話,那麼,六十年代的現代主義小說,更側重的是書寫個人的心靈史,展示個人的存在狀態,表現都市生活的感受、體驗。這些作品最主要的共同特徵,就是極力挖掘人的主觀世界,表現人的直覺乃至變態心理和潛意識活動,極力表現出荒誕社會中的荒誕人生、港人的生存困境,塑造了一個個尋尋覓覓,尋找自我、尋找歸宿的精神「酒徒」。故此,我將這類文學現象視之為香港現代主義小說中的「酒徒現象」。
香港小說的這種現代性轉變,突出地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新的感知方式,展示形形色色的都市生活形態,表現都市風、時代感,寫出人與人之間的疏離關係;二是真切表現人的內心精神世界,探討人的複雜心理,關注自我的存在狀態。從這個角度來說,劉以鬯的創作無論是內蘊還是藝術表現形式,都體現了一種「現代性」,是香港現代主義文學的先鋒。
劉以鬯的小說創作還具有相當的社會意識,對各種社會現象作出直接而及時的反映,如〈動亂〉以擬人的手法,反映六七暴動的亂象。作品通過一些無生命之物,如吃角子老虎機、石頭、汽水瓶、垃圾箱、電車、郵筒、炸彈、街頭,乃至屍體等,見證了血腥的暴動所造成的傷害,以不帶作者主觀感情﹙或者說作者有意掩藏自己的判斷﹚的「零度」寫作方式,客觀「報道」了這場社會風雲。
八十年代,回歸在香港社會激起了千重浪,港人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歷史大考驗,「何去何從」成了每個人所關心思考的問題。劉以鬯以敏銳的觸覺,於1983年創作〈一九九七〉,塑造了一個對前途充滿憂慮、不知何去何從的港人形象。這又是一個開先河的作品,從此「九七書寫」成為香港文學的另一個主潮。
無論是「酒徒現象」,還是「九七書寫」;是內心獨白的意識流,還是物化視角或反覆敍事,劉先生都是走在前列的文學先鋒。
因為獨特以及走得太前而孤獨,又因為自得其樂而煢煢漫遊。(本篇標題書寫:謝有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