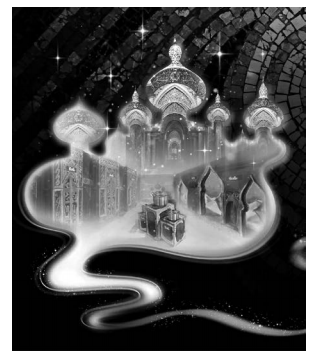主欄目:《香港文學》2018年9月號總第405期
子欄目:香港作家散文大展
作者名:何福仁
1
辛伯達(Sindbad)這名字在阿拉伯的世界,並不罕見,名馳天方之外,是因為《一千零一夜》這套書,其中有一位辛伯達講述他航海的故事,我這個聽者,另一個做腳夫的辛伯達,卻很少人記得,但你是辛伯達,我也是辛伯達,沒有我這個聽者,聽了再轉告山魯佐德,她即使已經採集了許許多多的故事,可以每夜告訴國王,足夠說一千零一夜,也未免失色。她說的故事可長可短,伸縮自如,每說到要緊關頭就煞住,另一個晚上再說,而且沒完沒了,這一個結束,就緊接另一個開始,吊盡了國王的胃口。這國王,由於王后的不忠,患上了可怕的仇女症,Misogyny,這詞是山魯佐德教會我的。他每天娶一個來過一夜,次日殺掉再娶,如是殺了差不多一千零一個。國裡的女子,不是被他殺掉,就是逃亡外國,只有山魯佐德自薦請求入宮。因為她會講故事。原來故事可以救人,另一面當然也可以殺人,分別是有的故事講得好,有的故事講得壞。山魯佐德的故事講得好,她啟示我們:好故事除了故事講甚麼,更重要的還是怎麼講,那是節奏,是timing。此外,在故事海裡,好像只有講者,沒有聽者,我們只看到一張張開合的嘴巴,沒有看到,或者根本忘了還需有配合的一雙雙耳朵。
講者怎麼講,以至講甚麼,也要針對聽者,要有講的策略。講者和聽者,一動一靜,可要互相照顧。山魯佐德真是聰明伶俐的女孩,《一千零一夜》說她熟讀各民族的文學和歷史,其實呢她更多的是聽做宰相的父親說的故事,從八歲到十八歲,全都牢牢記得,她是從聽故事裡學會講故事的。然後,她再聽到我的轉述。她是這樣四方上下仔細聆聽,當她自己成為講者,就加添了個人的想像,某些地方輕輕帶過,某些地方加添胡椒、丁香。她針兩個辛伯達何福仁,香港大學畢業,主修中國文學及比較文學。著有詩集《龍的訪問》、《如果落向牛頓頭腦的不是蘋果》,散文集《書面旅遊》。對的是一個權力最高、情智兩商都極低的聽者。她必須好好地掌握適時的停頓、展開。這裡面有逗引、媚惑、延宕、紓解。時間和節奏,好像說來誇張,是故事和說故事的人,生死存亡的關鍵,而她,掌握得分毫不差。在講述的過程裡,她表現出只她自己才有的言語魅力。我可以想像國王在聆聽時,目定,結舌,下顎禁不住下垂,他不再是國王了,不過是中了咒語的呆瓜,充滿對故事的期待與渴求。不過他也不是無藥可救的,他接受了一千零一夜的治療,終於不再殺人。他成為一個正常的聽故事的人。
辛伯達航海的故事,老實說,本來很平庸,那我為甚麼還要聽他的,很簡單,為了要尋找聽者,他每次總送贈一百金幣,又大排筵席讓人飽餐一頓。世間還真有這樣便宜的事。錢太多的人,寂寞、抑鬱,總有太多的話想說。不過錢太少的人,同樣寂寞、抑鬱,何嘗不多話說?只是沒有酬金,就難得有人聽他的。航海遇難的辛伯達,遇到拯救他的人,就不斷重複他的遭遇,有時重複多達四五次,要是山魯佐德原話葫蘆,毫無創意,豈不更令人煩厭?也許早就說者已死。所以她剪裁删減,能省就省。我可是沒有理由不聽他的,我只需聽他七次,已經可以成為帳篷旅舍的老闆了。我不是也開始講我自己的故事麼?這是另一個由腳夫講的故事,而且肯定會比航海的一個說得有趣,因為我不用再替人搬運跑腿了,我日間也開始讀書,讀不同的書,學不同的語文。我發覺想故事講得有內涵,唯有努力讀書,努力學習,並且無需刻意或者強調跳出一個阿拉伯人的視野而面向世界。相反,我寧願謙卑地把我熟悉的地方縮小,不過轉用一種陌生人好奇的眼光。因此,我居然可以通過說故事而收取酬勞呢。
我必須先交代故事的背景,因為我的聽眾已不限於阿拉伯人,更不限於穆斯林。阿拉伯半島大多處於熱帶沙漠氣候區,日間酷熱,晚上可涼快得多,有時彷彿跨進了寒帶。這時候大家放下工作,又捨不得睡去,就圍坐篝火聊天,分享日間的所見所聞,那是娛樂,也可以互通消息。一圈篝火,那是故事的驛站,好像後人辦的雜誌。到來的,有熟人,也有旅客,有的十分博學,可有的是上過學的文盲。人來人去,我見過太多不同性格的過客,搶着開腔的,內心深處最寂寞。每個人都是一個故事,是故事把人串連起來,除了偶爾有些脾氣暴躁,喜歡鬥嘴,大多變得親和,既是講者,也成為聽者,但只聽不說,也不相干。至於有人聽了,就時而搖頭時而點頭,指指點點,後來竟然就成為一種專業,而這,可是另外的故事。奇事奇聞,人世豈會少見呢,所以未必可以走出一個篝火的小圈子;相反,看似平淡乏味的故事,由於說得動聽,往往從一個沙漠,傳到另一個沙漠;從一頭駱駝傳到另一頭駱駝。所以你以為沙漠是沉默的,只見駱駝終日磨牙反芻着甚麼,那只是沙漠給你的錯覺,一如你以為沙漠是沒有文化的荒漠,不知動物極多,不過到入夜才開始活躍。
阿拉伯人當然是陸上的旅行家,其實也擅於航海,不過從沙漠、草原,轉到洶湧的波濤,駱駝轉換為船隻罷了。阿拉伯的古船,船板不用鐵釘,而由椰棕絲搓成繩子縫合,不分船頭船尾,一樣的通用。這是傳統智慧,它們固然不能跟後世的郵輪相比,也遠遠不及稍後中國鄭和的寶船。不過,我在篝火夜談裡聽到,為葡萄牙人瓦斯科.達.伽瑪(Vasco da Gama)領航,從非洲到印度的人,就是一個阿拉伯航海大家,叫艾哈邁德.伊本.馬吉德。伊本.馬吉德寫過航海的書。他的書真難找呵。
阿拉伯人會航海,也嚮往航海。辛伯達航海的經歷呈現了阿拉伯人另一面的生活和傳說。他告訴你海洋是危險的,難以預測,卻是新奇的探險、挑戰,而且可以發財。說兩句我特別的體會吧。海洋是貓,深奧得很神秘,又神經質的單純,平時柔順,卻可以很兇惡,絕不好欺,牠畢竟是獅子老虎的堂兄弟姊妹。狗呢,屬於沙漠,莊嚴,好看,看來老實忠誠,但沒有個性,乏味,你試扮演阿拉伯的羅倫斯,早晚騎駱駝放風三天,就會知道了。我是否岔開了話題?不是的,你以為只有波斯人才愛貓?你以為故事有固定的結構?辛伯達每次歷險歸來,陸上生活一久,就覺得枯燥沉悶,於是又再出海,讓他可以帶回更多的故事,在篝火夜談裡,成為主角,分派每位聽者一條羊腿或者羊髀,給最好的聽者一百個金幣。他終於得償所願,在《一千零一夜》裡成為相當重要的一章,讓他以第一身自述。不過這位辛伯達七次航行,總是一樣的模式:出海、遇險、獲救、回家。許多名流富豪的自傳也總是這樣。幸好這些素材,由山魯佐德轉口,再經過另一個聽者,別忘了在國王和山魯佐德之外,還有那麼一位在場的隱者,他一直在聆聽,也一直在記錄。到頭來,哪些是水手的,哪些是複述,哪些是筆錄,再分不開來;加上如今再由我講述,一個聆聽的辛伯達變成講故事的辛伯達,為免拾人牙慧之譏,我好壞總得有一點個人的講法。總之,故事從口述到寫定,經過多少加減增删,轉接層疊,已無所謂原汁原味了。但也因此可以不斷講下去。如果你覺得有趣,像那個呆瓜的國王,覺得趣味就在所遇既離奇又魔幻的險境裡,讓我告訴你,這些並非全無根據,希望你記得在一千零一夜裡,有過一位記錄故事的聽者,而他可能只是一個被割了舌頭受了腐刑的黑奴。
2
辛伯達第一次乘船出海,航行了若干天,經過一個小島,看來很美麗,於是靠岸停泊,旅客都登上岸上舒伸,有的隨意觀光,有的洗滌,更有的燒火煮吃,各適其適,都很高興。忽然船長大叫:快快上船!扔掉一切,為了保命!原來那不是島,而是一尾大魚,漂浮久了,身上堆滿沙土,長出草木。因為有人在脊背生火,熱灼了,就潛下水去。旅客都墜入水裡。盤,才不致下沉。他應該精通泳術吧。船長卻不顧旅客,揚帆走了。
把巨魚當小島,在島上煮食,船長溜之大吉,我在篝火夜聚裡就聽過一位曾在中國生活的穆斯林說過,這位穆斯林老人說他年輕時遵從聖訓:為了尋求學問,可以遠至中國。他到了廣州,生活了數十年,認識其中一位在穆斯林教友中最受歡迎的阿布.宛葛素,宛葛素病逝後就葬在廣州的桂花崗,這墓園逐漸成為當地有名的「清真先賢古墓」。航海的辛伯達,要是不為獵奇,也走去參拜一下,事本尋常,反而叫人驚嘆。老人會讀漢文,看來已四五百歲,他帶回了不少筆記故事書,據說漢朝一位中國學者劉歆也寫過這樣的故事。而這位學者不可能看到《一千零一夜》。老人說,《一千零一夜》流傳許多年,最初寫成波斯文,後來再譯成阿拉伯書本。
至於阿拉伯人到中國,最早大概在唐朝高宗皇帝時期,有的從陸上的絲綢之路,可有的從海上的香料之路,那是從波斯灣出發,經印度,繞過馬來半島,到達廣州。廣州是阿拉伯人去華的大站。去華的目的,老老實實,是做買賣,阿拉伯人並沒有白人的擔子,不過穆斯林聚居自成圈子。不似哥倫布等騙徒,為的是黃金、土地,卻號稱傳教,船上可沒有一個傳教士。辛伯達走的,就是香料之路,他自稱從巴格達出發,巴士拉上船,航入阿拉伯海,一路向東,經過的地方沒有點明,都是荒島,然後到了城市。但那些地方,顯然是印度、馬來半島,最後是中國。
阿拉伯人書寫的遊記曾記一個盜鹽的頭子在廣州屠殺外僑信徒,單是穆斯林就殺了十二萬之眾,並且斬砍桑樹,刻意破壞絲綢的貿易,漢人的史書反而沒有記載。老人過目不忘,他解釋,這頭子叫黃巢,漢書倒記他一再屠城的故事,一次圍攻陳郡,一年攻不下,就每天捕捉數千百姓,監禁到「舂磨寨」裡,這是比後來希特勒的集中營更恐怖的營寨。甚麼是「舂磨」?一個嘴叼在烤羊腿的少年問。那是用來搗米的大舂碓,黃巢特製了數百個放置在營寨,但舂磨的不是米,而是人,把生人納入其中,用舂磨碎,連骨肉一起,吃了。
在第三次旅程,辛伯達也遇過一個吃人的巨人,但最恐怖的吃人的故事,出現在第四次。他航行時照例遇上風暴,和其他旅客流落一個不知名的荒島,被一群人送到國王那裡去。國王送上食物,讓他們大吃特吃,愈吃愈想吃,變得神志不清,瘋瘋癲癲,還被灌飲椰子油,並且塗身。然後,挑最肥大的,殺了,供國王享用。辛伯達沒有吃,他只是一隻瘦鴨,所以沒被選中吃掉。他之前沒被巨人吃掉,同樣是因為骨多肉少,不合美食的要求。
但這個航海的辛伯達自己也殺人,殺了不少人。同樣是第四次的旅程,他把兩個故事擠在一起講,到了第六次,就乏善可陳了,只好重複第二次看見巨大的神鷹,誤當神鷹蛋是一座巍峩的白色圓頂建築,光滑、圓潤,他無法攀緣上去,卻又找不到大門。故事有趣,只是重複出現,說明他其實並不懂得分佈情節。他逃出了吃人國,不多久到了另外一個繁榮的地方,又被送到國王面前。要注意的是,外地的國王,比天方自己的親民得多呢,尤其對訪客。由於他會替國王做馬鞍,國王就把一個美麗的富家女許配給他。但且慢高興,那裡有一種夫婦殉葬的傳統,一半死了,另一半就得陪葬。殉葬,是當年印度的習俗。他的妻子不久病死了,他被迫殉葬。死者都葬到高山上一個深井似的大坑洞裡,他被扔進去,放下一些飲食,再用大石蓋上洞口。這一次,他看來死定了。不過到飲食將盡,又有女子被扔進來陪葬,他拎起死人的骨頭打死她,奪了她的飲食。如是見一個殺一個,人家的喪禮,成為他活命的源泉。老人告訴我,許多年後一位英國紳士跟人打賭,要在八十天裡環遊世界,他途經印度,順便挽救了一位要陪葬的年輕寡婦,並把她帶到英國上流社會去,充分表現了白人優越的「文明」與「正義」。美國的內戰,不過比出發環遊世界的英國紳士早十年,你以為那是真的為了解放黑奴而戰?抑或是經濟問題,美國南北不同發展的對決?老人的問題很超前,如果我們也有四五百歲,也許會知道答案。
另一次,在辛伯達遇上海老人,他應老人的要求,揹起老人過河,誰知過了河,老人不肯下來,反而雙腿緊纏他的脖子,老人的「兩隻腳黑得像水牛蹄子」。他就設計灌醉老怪物,用石頭照準他的腦袋砸殺了。他第三次航行,經過「猿人山」,他講述猿人的樣子,「頭髮好像獅鬃,形狀可怕,眼黃面黑,身材短小」,這不就是後來僅存在婆羅洲、蘇門答臘的紅毛猩猩?第五次奇遇,他講學會了採椰子的辦法,不用上樹,只需用石頭扔椰樹上的猴子,猴子就會用椰子反擊,這辦法後世沿用。椰子樹在熱帶或亞熱帶地方生長,原產於馬來群島。他描述好幾個地方出產檀香、沉香。
第七次,最後的一次,他遇難後又誤打誤撞,到了一個建築美麗、人煙稠密的大城市,一個慈祥的老人帶他回家,給他飲食,然後由婢僕端熱水給他漱口洗手,拿絲帕給他擦手,招待他住在屋子的側室,這顯然是中國人的做法。他在荒島收集檀香木編製的小船,賣了個高價。而且,這一次,老人又要把獨生女兒嫁給他,還打算將來由他繼承產業。當年我聽到這裡,就禁不住對他仔細打量,真是個好運氣的傢伙。他接着告訴我們另一個奇異的事,當他和城裡的人來往,發覺他們每當月初,身上就長出翅膀,可以在空中遨遊。他請求其中一個,讓他騎在肩上,帶他在天空中開開眼界。你知道,阿拉伯人走遍海陸,就是還不曾飛上空中。太奇妙了,在空中飛翔時,他不禁驚呼讚美阿拉。可這麼一喊,空中就出現火燄,他們急降到一座高山上,他們生氣極了,把他撇下走了。後來,他的妻子告訴他,這些飛行的人不信安拉,是魔鬼。他們當然不是魔鬼,只是不信教罷了,辛伯達在海上轉悠,他們則在空中,並不害人。
辛伯達遇到的,的確不全是魔鬼、怪物,每次陷入困境,總獲得善人的拯救,他失去的貨物,又往往獲得歸還。但故事充滿吃人、殺人,加上《一千零一夜》裡不少性的描寫,其實只宜成人。事實上,二十世紀後,《一千零一夜》在1985、2010年前後兩次在埃及被心智幼稚卻道德超標的人控上法庭,罪名是語言淫穢、違反道德禮教。當然,最後都獲判無罪。小說家馬福茲曾為此辯護,指出經典不能禁,不過可以有兩重面目,一個删節本,讓普通讀者親近;另一個完整的版本,讓成熟的研究者研讀。《一千零一夜》裡至少有兩個辛伯達,為甚麼不可以有一個平易近人,另一個有點神秘,又有點嚴肅?記得馬福茲嗎?愛聽故事的人都記得。他又曾為魯西迪的《撒旦詩篇》發聲,認為雖然冒犯了先知,可也不能因此被追殺。他認為異見是必須包容的,發出追殺令的霍梅尼其實是恐怖分子。這令人想到,權力並不令人成為理想的聽眾,要是沒有一兩個山魯佐德的治療,還是不要聽故事才好。結果呢,馬福茲挨了激進分子兩刀。他生前一直住在開羅,足不出外,諾貝爾文學獎還是由他的女兒去領。他寫的故事也從沒離開古今的開羅,那裡的小市民、大街、小巷,那裡的聲音、氣味。
《一千零一夜》,又叫《天方夜譚》,譚不叫談,是為了避一位國王的諱,中國人讀到的,譯本多達四五百種之多,據說大多是抽取個別的故事,納訓的一套六本,故事都在裡面了,可仍然只是潔本。換言之,中國人始終停留在聽奇情故事的水平,因為最重要的,山魯佐德說到故事高潮時延宕的高妙技巧,潔去了。
那麼記大魚當小島,是阿拉伯人在中國聽到的傳聞,再傳回來麼?中國的學者推測,故事最初可能來自印度的佛典。故事,原來也擅於旅遊,遊到了喜歡的地方,就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