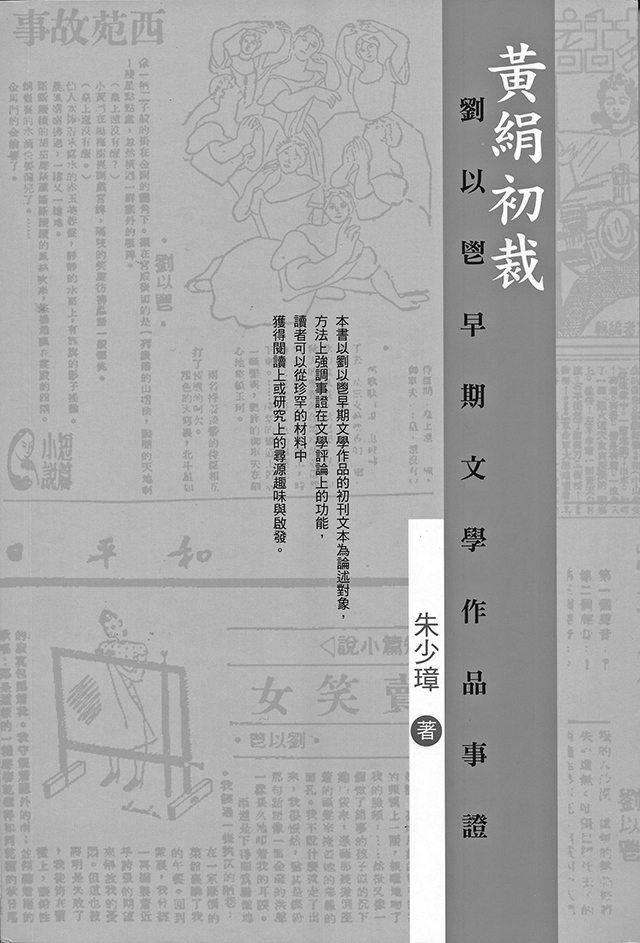主欄目:《香港文學》2020年6月號總第426期
子欄目:紀念劉以鬯先生特輯
作者名:朱少璋
為劉以鬯研究添磚
年前聽聞內地會出版一套多卷本的劉以鬯全集,萬分期待,但編刊工程相當浩大,未知能否在短期內成事。2020年筆者暫據個人蒐集所得,以「劉以鬯早期文學作品事證」為專題,寫成了《黃絹初裁》;小書一部,希望能為將要陸續開展的劉以鬯研究添磚。此書以二十二個別具事證價值的劉氏早期文學作品為討論中心,這些材料既可視為劉氏漫長創作歷程的近源坐標,復能較具體或較全面地展示劉氏在詩歌、散文、小說、翻譯各方面的早慧丰姿。成書過程中,筆者深深體會到整理、處理劉氏作品的困難。下面以個人撰寫《黃絹初裁》的粗淺經驗為例,談談整理、處理劉氏作品的五個「難點」。
分時期之難
研究者多以地域劃分劉氏的三個創作階段,如鄭政恆〈劉以鬯一百歲〉:「簡單來說,劉以鬯經歷了中國大陸時期、南洋時期和香港時期,而最重要是香港時期。」如此一來,分期既有客觀標準,為何說「難」呢?其實,難點具體反映在個別作品的繫年問題上。
例如〈花匠〉在2010年輯入了《熱帶風雨》。《熱帶風雨》收錄了五十多篇小說,編者聲稱是五十年代劉氏「南洋時期」以「新馬」背景的作品;但〈花匠〉卻是誤輯入集的作品,這篇小說實初刊於1947 年的《人人周報(上海)》,當時劉氏尚未離開大陸。就作品分期而言,〈花匠〉是劉氏「大陸時期」的作品,並不是「南洋時期」的作品。至於〈花匠〉有否在劉氏「南洋時期」重刊過,則限於未見相關材料,未敢遽下定論,但〈花匠〉即使在南洋重刊過,在討論時若以此為例說明劉氏南洋時期作品的某些特點,則有欠穩妥。劉以鬯是多產的作家,又曾經在大陸、南洋及香港寫作,相信類似〈花匠〉在繫年、分期上的混淆或錯置的情況,所在多有。
尋初刊之難
「初刊文本」的鈎沉工作對整理一位作家的全集尤為重要,作品鈎沉的工作需要有步驟有計劃地進行,才有成果。例如陳子善在〈劉以鬯的《詩草》〉中談到劉氏發表於1947年《幸福世界》的一輯新詩,為讀者展示了罕見的材料,十分難得。陳氏還賞析了部分詩作,如〈淺夏〉:「此詩寫初夏雨夜,情景交融,詩句工整,而第二天雨過天青,『屋外太陽的手指』、『正在撥弄汩汩江水』,多麼生動形象,又多麼出人意表,同樣是一首意象奇特的好詩。」小說家的新詩,將來都一定要編進全集中去的。但陳氏在分析時卻忽略了〈淺夏〉發表於1946 年《和平日報》上的初刊文本(詩題是〈淺夏小記〉)。初刊文本除了在個別措詞上與再刊文本略異,還比再刊文本多出了一句「淺夏送來一份寥落」,有了這一句,全詩顯得更切題、更完整;讀者若只以重刊文本為據作分析,恐怕不得要領。而這首初刊的〈淺夏小記〉與再刊的〈淺夏〉,他日在編入全集時,又到底應以哪一種方式向讀者展示?是兩作並列?還是以校記交代異文?又或者只刊其一?
有經驗的讀者或研究者都知道,書籍的初版信息可以根據原書的版權頁或牌記確認,起碼有個記錄,有個根據。但在刊物上發表的文章到底是否「初刊」則較難百分百確認。雖說作者一般不會再刊同一個作品,但也會有例外的個案,不能一概而論。比如劉氏在1945年的《文藝先鋒》上發表的〈地下戀〉,這篇小說後來易名為〈露薏莎〉並略作修訂,分兩期在1948年的《幸福世界》上再刊。那是說,〈露薏莎〉(或〈地下戀〉)在成書前,就曾在兩份刊物上發表過。若按「初刊」的原則及定義,1945年的〈地下戀〉較1948年的〈露薏莎〉發表日期要早,因此1945年的〈地下戀〉就是「初刊文本」。可是,將來會否發現另一個比〈地下戀〉更早發表的文本呢?這不能說絕對沒有可能――未發現不等如沒有――上文說「在刊物上發表的文章到底是否『初刊』則較難百分百確認」,就是這個意思。正如上文所說,他日在編刊全集時,〈露薏莎〉和〈地下戀〉兩個大同小異的文本,到底應以哪一種方式向讀者展示?是兩作並列?還是以校記交代異文?又或者只刊其一?
辨改寫之難
「改寫作品」可視為劉以鬯創作特色之一。這裡說的「改寫作品」,意思是作者改寫自己的作品,使之變成另一個文本。
劉以鬯在《劉以鬯卷》(三聯版)的自序中曾談及個人創作中的「改寫」個案,他提及〈對倒〉和〈蟑螂〉:〈對倒〉(《四季》版)是長篇改短篇的例子;〈蟑螂〉是長篇改中篇、中篇改短篇的例子。像這些「改寫」個案若經劉氏本人證實,研究者在整理材料時總有個根據,但劉氏沒有提及的「改寫」作品,相信尚有不少,研究者必須在這方面多加注意。例如論者向來都視〈風雨篇〉為一個完整的獨立文本,但卻沒有留意到〈風雨篇〉與〈夢裡人〉的改寫關係。〈夢裡人〉(初刊於1947年)在〈風雨篇〉(初刊於1946年)的基礎上多出了近三千字,是由微型小說改寫成短篇小說的例子,事涉「擴寫」、「增補」,在劉氏創作活動中,是頗具特色而又成功的創作試驗。可惜一直以來〈夢裡人〉都給讀者遺忘了,連劉氏本人都好像忘記了這篇小說。像這些重要而具研究價值的改寫線索,尋索維艱,但必須細心又耐心地去做,才能較全面地回復劉氏創作的面貌。
求全整之難
許定銘曾在〈關於《劉以鬯全集》的建議〉中談及編刊「劉以鬯全集」的構想:「我希望這套將面世的《劉以鬯全集》,是套真真正正的『全集』而不是『選集』。過去有些嚴肅文學作家在出版全集時,往往故意漏掉某些不滿意的作品,又有些喜歡把處女集定於成名後的某部作品,而蓄意把以前學習寫作時期的習作刪掉……」其意見值得肯定,筆者就找到劉氏十三歲時發表的散文(〈默念〉)、十五歲時發表的小說(〈乾魚〉),以及十六歲時發表的徵文參賽作品(〈荒後〉)。這幾篇「少作」固然稚嫰,但卻有力而具體地展示了劉氏學生時期的創作風貌,是劉氏早期創作的重要材料。討論或分析時固然不應繞過這些「少作」,編刊全集時更應盡可能把這些「少作」都編進書中去。
有關「求全整」,尚有一個難點要提出,就是由劉氏撰寫的一些「非文學」作品,到底是兼收並蓄,都收進「全集」中去?還是把「非文學」作品都擯於集外呢?文學作品泛指詩歌、散文、小說、劇本、翻譯,這些作品相信都肯定會收入全集。但非文學篇章又該如何處理?比如筆者在1940年《中美周刊》讀到一篇署名「同繹」的長文〈傘兵戰略與國際公法之探討〉,此文屬於非文藝作品的軍事評論。又如1945年《光》的「星座」欄目下,有署名由「劉同繹」或「劉同繹、陶啟湘」選輯的列國趣聞與掌故,但由於署名下說明是「選輯」,而原文內容則是選輯者過錄或摘抄的材料,性質上肯定不符文學作品的標準。復如劉氏在辦報時為某些欄目撰寫「編者話」一類的短文或按語,由劉氏主理編務的《和平日報》上就有不少與「編者贅言」相類的材料,從廣義上說,這些短文可以算是散文中的「雜文」嗎?這一切一切,都有待各專家作深入的討論,但無論是取是捨,都肯定極花心思。
證事實之難
劉氏生前通過撰文或接受訪問,都直接或間接談及個人的創作歷程。作者現身說法,所提供的信息固然是研究劉氏的重要材料,研究者向來都重視。但基於種種原因,作者的說法也可能有失實之處,研究者必須細心查證,確認事實,才好引用。
如1980 年《開卷月刊》雜誌訪問劉以鬯,直接就「發表起點」問過劉氏,劉氏的回答是:「我第一篇小說是在讀初中時寫的,登在朱旭華先生編的《人生畫報》上,寫得很幼稚。」九十年代劉氏在《劉以鬯卷》(三聯版)的自序中再一次清楚地確認〈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的「最早」身份,強調這是「最早的短篇小說」。易明善在《劉以鬯傳》中即據劉氏的說法,說〈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是「劉以鬯在報刊上發表的第一篇小說」。經劉氏自述而復經易明善在《劉以鬯傳》中的轉述,視1936年初刊的〈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為劉氏短篇小說的「發表起點」幾乎已成定調。
查〈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刊載於1936年5月《人生畫報》,而劉氏另一篇鮮有論者(包括劉氏本人)提及的短篇小說〈他們的結局〉則分兩期發表於1936 年2月、3月的《時代知識》上。那就是說,〈他們的結局〉初刊較〈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早兩至三個月。據此,若說劉氏發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是〈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說法並不符合客觀事實。
又如劉氏在2015年為「劉以鬯文集」(未刊)寫的〈致讀者〉中,有「我十八歲始發習作」的話(《城市文藝》第96期),類似的說法還見諸劉氏其他文章,而論者亦多以劉氏的說法為據。但事實上,筆者目下找得到的劉氏早期作品中,散文〈默念〉發表於1932年,當時作者只有十三歲;小說〈乾魚〉則發表在1934年,當時作者是十五歲――可證劉氏「我十八歲始發習作」的說法,與事實並不相符。
劉氏為何會忽略了〈他們的結局〉、〈默念〉及〈乾魚〉呢?是忘記了?還是另有原因?相信這是研究者可以進深探討的有趣課題。
結語
劉以鬯的創作理念是「與眾不同」,那麼,有關劉氏的作品整理計劃或研究工作,是否也該有點「與眾不同」?期待各專家深思、跟進――為將要陸續開展的「劉以鬯研究」,做好準備。相信本文提及的種種具體問題,可以讓我們更清楚知道與劉以鬯相關的研究到底要克服哪些困難。有了這些困難作為明確的標幟,研究者只要「知難而進」,假以時日,相關的整理或研究成果,必然豐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