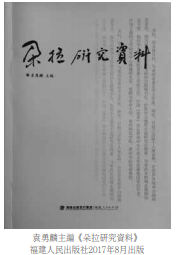主欄目:《香港文學》2018年3月號總第399期
子欄目:特約書評
作者名:陳志文
朵拉,馬來西亞華文女作家、畫家,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涉足文壇,四十多年來筆耕不輟,出版過幾十部文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起就有學者撰寫朵拉的研究論文,歷經二十餘年的積纍,已有了較為深厚的積纍。但由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特殊性與跨國界性,各種資料收集與整理的難度與單純的國別文學研究不可同日而語,「史料學的建設仍不盡如人意」(1),「相對史料散佚、湮滅的速度,史料收集、整理的進程顯得過於緩慢」(2),對朵拉其人其作品,不少研究者也是知之不多,許多學術成果也正是在這種「不識廬山真面目」的情況下篳路藍縷,艱難展開。資料是所有學術研究的命門,資料的匱乏必將制約學術的發展,因此對朵拉的生平、作品、創作思想與相關研究等進行梳理與整理,已經成了朵拉研究迫在眉睫的要務。十分有幸的是,我們看到了袁勇麟教授主編的《朵拉研究資料》2017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朵拉研究資料》是目前第一本朵拉研究資料匯編,其中涵蓋了研究文章、訪談、回憶錄等敘事性史料,以及年表、索引等工具性史料,多種史料的匯聚與精當合理的組織安排使得全書洋洋灑灑,蔚為大觀。《朵拉研究資料》既相容了現有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與研究成果,又在此基礎上有所創新與發揮,可謂承上啟下,意義深遠。
1 鏡與燈:他人印象與自我表達的輝映
作家的序言,他人的印象或採訪等史料,在書籍排版印刷時就區分於正文,讀者在閱讀時往往容易忽略。不僅如此,在某些研究者眼中,這些史料往往也屬「邊角餘料」,其重要性與作為正文的文本不可同日而語,因此一些資料集在處理史料時,對敘事性史料採取了有意或無意的忽略與遮蔽。事實上,敘事性史料對研究作家作品往往有着非同一般的價值,通過作家的自敘與他人的印象,能夠更好地「以意逆志」、「知人論世」,這種方法雖然在二十世紀「文本自足」、「作者已死」等大潮的衝擊下顯得略為古舊,但千百年來的文學批評實踐也證明了這種闡釋方法的有效性。也許正是因此,袁勇麟教授在處理敘事性史料時,不僅採納了他人的印象、訪談等史料,同時也相容了朵拉自己的聲音。《朵拉研究資料》的第一部分「朵拉創作談」與第二部分「印象與專訪」,分別收錄了朵拉文集的序言、後記等創作談,以及他人為朵拉作品作的序和對朵拉的採訪等內容。
美國文論家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中闡述了西方文論中「鏡」和「燈」的隱喻,「鏡」旨在強調心靈對外部的反映,而「燈」則說明了心靈的自我表達。如果我們借用這一由來已久的隱喻來觀照《朵拉研究資料》,就會發現,「朵拉創作談」是朵拉點燃心燈的自我展現,而「印象與專訪」則是他人眼中朵拉的鏡像,燈影鏡影相互交織,最終形成了「對話」而非「言說」的效果,這就為我們瞭解朵拉提供了多維的視域。閱讀第一部分後,我們可以發現,朵拉的自敘大多是其創作理念與生活經歷的陳述。例如,朵拉在〈問世間,情是何物〉中,直陳自己的創作觀念:「寫作不一定是為了名垂千古,說是為了利便更可笑了。」又如在〈遲開的小花——小說微型〉中,朵拉也談及了自己對微型小說的看法:「字數少,篇幅短,因此微型小說必須在有限的信息範圍內,給予讀者最廣闊的想像空間。」而他人的印象則多是對朵拉作品和朵拉本人的直觀描述,例如姚拓在〈生女當如小朵拉〉中寫道:「微事中見啟示,挫折中見新生,失意中見同情,忍讓中見美德,都從朵拉的筆尖流露出來……」又如戴冠青在〈溫婉優雅的智慧女性〉中這樣形容朵拉:「這就是朵拉,一個溫婉優雅、富有才情、隨緣而執著、從容而淡定的智慧女性。」如果只有作者的創作理念與生活經歷,我們就無法瞭解作品與作者本身的特徵;同理,如果只有他人印象式的感受,我們又將陷入不知作者真意何在的泥潭中,因此只有將兩者結合,我們才能更加清晰地觀察到朵拉其人其書的全貌。同時,「鏡」與「燈」並不是兩條互不干擾的平行線,自我表現與他者印象之間的互文、對話甚至碰撞也能讓我們更加深入地走近朵拉,例如在〈《十九場愛情演出》之外〉中,朵拉曾透露自己渴望突破創作方向較為單一的局限,「我創作的方向,是不是應該有所轉換了?」而在小黑的〈不是反調〉中,小黑就已經暗示了朵拉的「文學野心」:「真是要寫作,寫寫流行的愛情吧。那豈不是更加風光?何必處心積慮,辛苦經營。但是她卻是一個自命清高的人。她抱着對愛情同樣執著的決心要寫出一個春天,真拿她沒有辦法。」
總而言之,自我表現與他人印象的相互輝映,照亮了朵拉其人其書的多個層次,而非一個維度一個視角下的一家之言,這就為日後的研究者們提供了更為寬廣的視域與更為新穎的闡釋向度。
2 史與論:專題史料與學術研究的合璧
學術研究講究「史論結合」,「論從史出」,缺乏史料的論述如同空中樓閣,而缺乏論述的史料同樣也僅僅是一盤散沙。從某一作家生活經歷與創作歷程的「史實」出發推及到從學理上對作家的「史識」,本是一件極其自然的事情,港台許多華文文學資料匯編正沿用了這一體例。然而大陸現有的許多研究資料,要麼是流於「純粹歷史」的資料匯編,要麼則是單純的論文集或學術史梳理,史料與研究,總有一個處在缺席與沉默的尷尬之中。作家生平等第一手歷史資料之與學術研究的重要性自不用多言,而實際上,作為研究的學術史同樣也是史料建設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因為學術活動的繼承性與連續性要求每一個研究者心中必須有着研究對象的學術前史,唯有如此方能推陳出新,所以優秀的作家研究資料就需要不僅做到對作家作品資料的收集與整理,同時也需要做到對作家研究史的梳理與總結。《朵拉研究資料》正是如此,本書既收錄了作者年表、照片等史料,也按時間順序收錄了幾十篇有關朵拉作品的文學批評及學術批評文章,選文精當,提要鈎玄地概括了迄今為止朵拉研究的全貌。
除了上文涉及到的「朵拉創作談」與「印象與專訪」,本書中有關朵拉的史料還有數張珍貴的照片以及朵拉文學創作與活動年表。尤其是「朵拉文學年表」,這一部分採取的組織形式有別於傳統的表格,而是採用了散文敘述的方式簡要概括朵拉的生平事蹟、文學創作與社會活動等事件,由朵拉熱心組織和參與世界華文文學的各種活動與會議,朵拉的活動幾乎將近年來世界華文文學的重大事件串聯成一條相對較為清晰的脈絡,因此對朵拉的文學活動進行梳理,其意義就不僅僅限於朵拉一個作家,同時也在對近年來世界華文文學發展歷程的梳理與回顧。
同時,《朵拉研究資料》還按時間順序精選了近五十篇有關朵拉的文學批評與學術批評文章,評論對象包括了從朵拉早期的愛情小說到近年來的散文集與水墨畫集,大致勾勒出了朵拉創作重心的變遷與學術界與評論界對朵拉作品研究與評論的發展歷程。閱讀這一部分後,便能對朵拉研究的歷史與現狀,成就與不足有一個大致的理解。簡單來說,對朵拉的評論是從朵拉登上馬來西亞文壇開始就同步進行的,而對朵拉的研究則稍稍滯後一些,但歷經幾十年已經有了較為豐厚的積纍,可以說基本涉及了朵拉幾乎所有重要的作品。更難能可貴的是,不少評論文章能自覺地追求學術上的創新與變革,擁有較強的理論意識與問題意識。
將朵拉的生平經歷、創作歷史與對朵拉的評論文章融為一爐,兩者相輔相成,不僅有助讀者加深對朵拉的理解,更有助研究者們對朵拉其人其書及朵拉研究的學術史建立一個較為清晰的脈絡,《朵拉研究資料》可謂一次史論結合的有益嘗試。
3起與承:話題開拓與史料傳承的融匯
目前學術界已經可以說對朵拉進行了相當的研究,但工具性、基礎性的資料匯編類書籍卻依舊闕如,這實際上制約了朵拉研究的繼續深入與發展,影響着後續朵拉研究的高度與深度。作為第一本系統的關於馬華作家朵拉的史料以及論文匯編,《朵拉研究資料》填補了這一空白,它既是一本工具書,也是對迄今為止朵拉研究的小結,對今後的朵拉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同時,《朵拉研究資料》也是「世界華文文學史料叢書」的第二本,繼承了《陶然研究資料》的體例與範式,兩書一同形成了一個較為穩定的體系,為今後的世界華文文學史料建設提供了一個可資參考的樣式與值得學習的榜樣。
在中國知網等學術引擎上,已經有數十篇關於朵拉的研究論文,近年來還有不斷增長的趨勢,更值得關注的是,2016年起已經出現了關於朵拉的碩士畢業論文,由此可見朵拉研究與評論已經不單單只是學者與評論家們在期刊上的孤軍奮戰,而是已經滲透到了學生們的研究視野,研究生是學術研究的生力軍與新鮮力量,他們的加入使我們看到朵拉研究廣闊的前景。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的朵拉研究存在着研究角度單一,研究方法陳舊,研究結論重合等問題,大多數論文仍停留在就文章論文章的階段,缺乏鞭辟入裡的思考與開闊的視野,這當然有研究者自身的原因,但由海外華文文學的特殊性質,資料的匱乏其實也大大限制了相關研究的深入。舉例而言,朵拉身為馬來西亞華人作家,大陸的研究者又多半對馬來西亞這一國家的大致情況乃至該國的文學生態知之甚少,文學有其生長的土壤,如果沒有對馬來西亞這一孕育朵拉文學土壤的瞭解,要得出對朵拉的作品有獨到而深刻的見解就顯得十分困難。又如朵拉的作品大多在海外出版,在中國大陸能夠直接購買到的書籍僅僅是朵拉作品的冰山一角,如此一來,研究者們就難以梳理出朵拉創作的發展脈絡,其研究就往往呈現出見樹不見林的遺憾。由此可知,作家朵拉資料的匱乏直接影響了相關研究的深度與水準,而《朵拉研究資料》的出現,真可謂解決了朵拉研究的燃眉之急,為朵拉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世界華文文學的史料建設,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但世界華文文學不同於現當代文學之處就在其越境性,越境導致了華文文學史料的建設「不僅需要大量的人力、財力,而且更需要『甘坐冷板櫈』的奉獻精神。」(3),袁勇麟教授板櫈甘坐十年冷,終將自己的史料學思想轉化成了華文文學史料的一系列結晶。通過相容表達與印象,史實與史識,袁教授出色地完成了《朵拉研究資料》的編撰工作,而《朵拉研究資料》自身,不僅是大陸出版的朵拉研究資料匯編的開山之作,又是大陸華文文學史料建設的接力之作。它的問世,不僅對朵拉研究有着深刻的意義,對整個華文文學史料建設,也有着里程碑式的意義。它與《陶然研究資料》一樣資料收集豐富、考據嚴謹、體大而慮周、意深而旨遠,形成了一個被實踐證明可行又較為穩定的體例,它們既是袁勇麟教授華文文學史料學思想的實踐結晶,也為世界華文文學史料的建設提供了一個系統而優秀的範本。袁勇麟教授相容並包、推陳出新的治史思想和甘於寂寞、默默奉獻的治史精神,也值得我們後輩學人學習。
【註】:
(1)袁勇麟:《關於世界華文文學史料學的再思考》,見《華文文學的言
說疆域:袁勇麟選集》,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頁4
(2)王婧蘇:〈言說世界華文文學的二元張力結構——評《華文文學的言
說疆域:袁勇麟選集》〉,《福建教育學院學報》 2017年第2期
(3)袁勇麟:〈關於世界華文文學史料學的再思考〉,見《華文文學的言
說疆域:袁勇麟選集》,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頁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