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欄目:《香港文學》2018年10月號總第406期
子欄目:散文
作者名:繆玉
到達南非德班市那天是6月20日,沒錯,至今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那個日子,因為再過兩天就是我的生日。我生日那天總能趕上夏至日,而夏至是大節氣,習俗上這天做些好吃的,北方在這一天通常喜歡包餃子,至於為甚麼,沒人能說得清楚。我走前母親一直嘮叨的一句話:「過了夏至再走唄」,可我那時每天都有送行的酒席,於是還了她老人家一句:「我已經提前過完了,你們在家吃吧」。許久後想,年輕真不懂事,不夠體諒母親的一番心思,不懂得「兒行千里母擔憂」的感受。
話說我到南非的目的是為了留學,可我的留學實在有點牽強,本來在國內工作不錯,不知怎麼就冒出了留學的想法。好吧,只盼着早日學成回國,讓自己再上一個台階。打定主意,便隨着好友一起,搭上了上世紀留學的末班車。
我這所學校前後有一百多名中國留學生,學校把我們集中安排住在一個公寓區,這樣一來同學們每天形影不離,除了在教室與授課老師說英文,其餘時間還是用中文交流。儘管老師總是在提醒「NoChinese」,可當同學們臉對着臉時,母語順嘴就溜出來,與在國內沒甚麼不同。
想來想去,決定離開這個環境,挑戰一下自己,否則在這樣的環境裡,我的英語一萬年也無法有突破性的進步。沒過幾天,在報紙上找到一處價格不菲的公寓樓房間,轉天便順利入住進去。
連陰雨已經下了幾天了,無論從哪個窗子望出去,外面都是一片白濛濛,天和地是連在一起的,看不到盡頭,就像我現在的心境。都說南非的自然環境和氣候是最適合人類生存的地方,而我此時卻無法感覺到,原以為躲過了北半球的酷暑,卻何曾想到南半球多雨的冬天更是寒在心裡。
學校已經開始放秋假,只好憋在房間裡背英語單詞,啃英語課文,天昏地暗沒有晝夜。
不知過了幾天,早上睜開眼睛的時候,發現天是大晴的,鳥兒也開始在樹上歡叫地聊天,煞是好聽。壓在心上的烏雲忽地一下散去了。吃完早飯,收拾停當,走出許多天沒有邁出的房門。當走到公寓樓門口時,突然頓住了,腳不知道該向哪個方向邁,第一次感到眼前的路陌生竟讓我手足無措。
我住的這個地方,是個放眼望去不見幾個人的小鎮,不是週末,整個鎮子像個空城,想找個搭訕的人都難。轉了個方向,還是走向那個剛剛搬來時買過食品和日用品的大超市。裡面總算是圈住了一些人,悠閒地在超市裡選購,我自然是閒逛,沒有可買的目標。
倒是一個正在擺放商品貨物的黑人大姐,熱情地向我打招呼,忽然心頭一熱,總算有人看到我的存在。我蹲下去用結結巴巴的英語跟她問這問那,她的英語我聽不太懂,只聽懂她是當地的祖魯人,在這裡做店員。她挪動着肥胖巨大的身體,拉着我來到一個桌子邊,那上面擺放了許多我沒見過的東西,她告訴我那叫牛肉乾,她拿起一小塊讓我品嚐,說實話不太吃得慣,可她的友好之情讓我感動。接着她麻利的打了一小包遞給我,我想是她在推銷吧,但是我願意接受她的推銷。想不到的是,這種南非特有的牛肉乾(Biltong),後來竟成了讓我想念南非的一部分。
我還是漫無目的的在裡面逛,最後買了些牛奶、麵包和零食,外加一個冰淇凌,無奈的走出了那個空大的超市。
在路過的一個花壇坐下,邊啃冰淇凌邊想着此時的同學們在做些甚麼,或許可以給他們打個電話,或許可以坐公車跟他們一塊去爬山或去海邊,晚上還可以去酒吧坐坐。剛想到這裡,冰淇凌啪地一聲掉在了地上,我也一下回過神來,不能,決不能,只要電話一通就等於走回頭路,就是前功盡棄。雖然自己還沒完全確定甚麼宏圖大志的偉大目標,也沒想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可是眼前的語言關是必定要過的,苦一苦就忍過去了。想罷,提起東西徑直又回到公寓樓的房間。
傍晚的太陽火紅地照射到屋子裡,我的眼神從書中拔出來,舉頭望了望晴朗的天空,可感覺那天空不是我的,沒有一絲的暢想。外面也開始有了喧鬧聲,那是孩子們的,樓下冰冷的游泳池裡似乎有人在游泳。不管是甚麼,反正都與我沒有關係。我這樣的對自己講。後半夜開始起風了,這就是德班特有的天氣,說晴說陰隨它變。風夾着大滴的雨點拍打着玻璃,我趕快去關窗戶,半個窗簾已經濕了,被風鼓起在半空中,外面的氣溫已經降得很低。不知道這場雨能下上幾天。我這樣地想。
果然,近乎是一個星期,太陽只在雲層中出現過幾次,其餘的時間整個世界都是在雨水中浸泡着。我的食品也快吃完了,空蕩的冰箱盡收眼底。
才短短的一個月,我忽然覺得自己要熬不住了,寂寞一天天的侵襲上來。人是怕寂寞的,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悟到。生長在喧囂都市的人們,是不會有這種體會。都說人怕失去自由,可寂寞一樣令人恐懼。
淒風苦雨的夜晚我開始哭泣,哭甚麼,連我自己都說不清。路是自己選擇的,沒資格怨別人。
從DVD機裡使勁抽出學英語磁碟,放上久違了的中文歌曲,沒想到竟是蔡琴的歌《庭院深深》。雖然這是一首愛情歌曲,可它的詞和調正如我與家人的感受,「這天上人間不能相聚,幾載的離散欲訴相思」。我已經不能自控,如珠般大滴的淚水奪眶而出。當唱到「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啊――不如歸去。」之時,我嗚咽着嗓音同時大聲唱了起來,那是我此刻的心聲。我要回家,回到有親人的家。
我恨自己,為甚麼沒有在臨行前與媽媽和家人吃那頓夏至的晚餐,那也是我的生日宴,哪怕只吃幾粒餃子,我竟是那麼不在意的錯過了。我想念家鄉的夏天,那是溫暖的夏天。我,悔恨難當。想到這裡,又一次的淚如泉湧。
伴着歌,伴着淚,我等待太陽出來,然後回家……
輕輕的敲門聲把我驚醒,不知甚麼時候我已經睡去了。打開房門是一個很老的卻又很體面的白人老太太,她慈祥地看着我,跟我打招呼問好,她告訴我她就住在我隔壁,昨晚我的歌聲和哭聲她依稀聽到,所以才來看看。
天呀,我竟不知自己的隔壁還住着這樣一個老人,從來路過她的房門時,門都是緊閉着的。她用手比劃着,示意我洗臉,再到她的家裡去。老人的房間和我的房間一樣大小,一樣的格局,可看上去雅致、溫馨,漂亮極了,每一個小物件都很講究。她稱自己的房間叫宮殿。從房間擺放的東西看,她是一個人住。老人的動作很遲緩,一邊燒着咖啡,拿着點心,一邊跟我聊着。她告訴我她叫玫瑰.瑪麗,後面那個姓我聽不清。我看着她,這麼好聽的名字怎麼也跟這位老太太搭不上,後來想想,她也曾經年輕過呀。
老人告訴我她有兩個兒子,都住在附近城市,但並不常回來。她今年八十四歲,已經一個人獨處很多年了,以前身體好時經常出去旅行,但現在動彈不了了。談吐中看出,她是個樂觀的人,她給我看她的照片,她丈夫的照片,還有兒子全家,話語裡聽不到一點對孩子的埋怨。一張張泛黃的照片,是她一生的故事,也像是一個世紀的縮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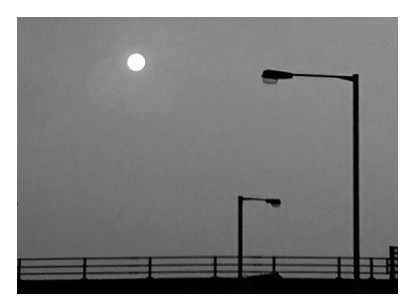
我看到茶几上摞放着幾本書,便問那是你在讀嗎?老人立刻說:「當然」,我翻了翻,都是小說,基本看不懂,她笑着說這些書她快看一輩子了,是她最喜歡讀的,現在她已經沒有朋友,只有這些書才是她永遠的朋友。我問她不寂寞嗎?她點點頭,又搖搖頭,笑瞇瞇的說,這是我的生活,我高興,我不喜歡去我兒子那裡住,或者甚麼地方,我享受我的生活,就像你也應該有你的生活。
在我快起身離開時,她拿出幾樣小禮物送給我,我推辭,太貴重了,她搖搖頭,並說:「我每天晚上睡覺時都會想,也許今天晚上我脫掉鞋子,明天早上上帝把我帶走,我就穿不上了,我會有一點難受。如果上帝沒讓我走,我就還會有明天,有明天就會讓我高興。」說罷她大笑起來,滿臉的皺紋堆積在一起,卻也十分燦爛。
我知道她是講給我的,因為她聽到了我的哭聲,她知道一個年輕女子想家人的心情。分手時她使勁的擁抱我,用手在我的後背撫摸輕輕拍打,像對待自己的孩子,我的眼淚又沒出息的掉了下來。
後來有幾次茶點接觸,我們一如老朋友般的暢談。快一個星期沒見她,正想着,房門被人輕輕敲響,我以為是老人來叫我,快活地跑去打開門,卻看到一個陌生男人立在門口,年紀在五十歲上下,他說他是隔壁鄰居,我立刻想到隔壁老太太的兒子,他接着告訴我他媽媽已經去世了,不知是哪一天,他今天來才發現,他是來跟鄰居們打個招呼。我心猛然一緊,雖然非親非故,在這段孤寂的日子中,她好像已經變成了我很親的人。她的話語和那張慈祥的臉,曾很深的觸動過我的心。我衝過去要看看,那男人攔住我,說人早就給抬走了。
我愣在那裡半天,抬走了,就那麼靜悄悄的抬走了,一點聲音也沒有,一個人就這樣消失了,從這個世界,永遠的消失了。我的心好茫然,想像着她應該是笑着走的吧。
我萎縮在被窩裡兩天,腦子一片空白。
快開學了,同學來電話要接我一塊出去玩,我,沒有拒絕。家人,友誼,陽光和新鮮的空氣是生命的一部分,這比甚麼都重要啊。我也應該有我的生活。說得對,我要出去,世間本沒有世外桃源,世界應該是多姿多采的,我的生活也該是多姿多采的,我必須要走出去了。
天,已經晴了,德班的天氣只要一晴溫度馬上升高,就如我心。是誰說:連雨不知秋去,一晴方覺冬深。而我好像已走過四季。我們奔跑在海邊,站在海灘,面對廣闊的大海,我在想,黑暗中我那點困難又算得了甚麼呢,只要有太陽,就會有新的明天!